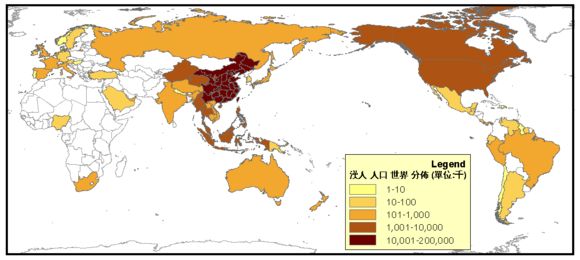
汉朝灭亡后进入汉人整合期(魏晋南北朝至清末以前),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大一统之后第一个大分裂的时期,同时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,“汉人”一词得到广泛应用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记》:兴平十一年,“三郡乌丸承天下乱,破幽州,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”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田畴传》裴松之注:田畴“出诱胡众,汉民或因亡来,乌丸闻之震荡.”《三国志·魏书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引鱼豢撰《魏略》:王莽时有人在辰韩之地“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,其语非韩人.问之,男子曰:‘我等汉人,名户来,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树木,为韩所击得,皆断发为奴.’”“胡众”与“汉民”并列,“韩人”与“汉人”对称,“汉”之族称含义显而易见.只是所记之事或发生在王莽之时,或发生在汉朝新亡不久,仍难脱“汉朝之人”之嫌。西晋末年,江统作《徙戎论》:“马援领陇西太守,讨叛羌,徙其余种于关中,居冯翊、河东空地,而与华人杂处.数岁之后,族类蕃息,即恃其肥强,且苦汉人侵之.”此乃江统为证其说而引汉朝故事,其中所称“汉人”之族称含义仍不十分确定。
晋八王混战,西晋被匈奴人灭亡,五胡十六国兴起,北方游牧民族鲜卑、匈奴、羯、氐、羌等入主中原,这是自华夏族形成以来的第一次(以后还有多次)。接着又出现了南北朝分裂对峙的局面,南方由汉人建立的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相继统治,北方由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、东魏(北齐)、西魏(北周)管辖.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,各民族的大范围流动、高强度对抗使得本已存在的民族称谓更加清晰.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改革,迁都洛阳,“班赐冠服”,改从汉姓,“断诸北语(鲜卑语),一从正音(汉语)”.孝文帝改革促进民族融合,强化了“汉人”的族称含义,陈连开先生认为,“汉人”确定无疑是民族名称,大概是在孝文帝改革的时候。魏孝文帝是对汉文化友好的君主,本民族自身文化落后,不汉化必不长久。
北齐时有个汉将高昂高敖曹随高欢讨尔朱氏,高欢对他说:“高都督纯将汉儿,恐不济事,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,于是如何?”昂对曰:“愿自领汉军,不烦更配.”高昂带兵有方,屡立战功,“于时,鲜卑共轻中华朝士,唯惮服于昂.高祖每申令三军,常鲜卑语,昂若在列,则为华言.”御史中尉“刘贵与昂坐,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,贵曰:‘头钱价汉,随之死.’昂怒,拔刀斫贵.”作为鲜卑化的汉人,高欢深知团结汉人的重要性,他在起事时就当众立下“不得欺汉儿”的规矩.坐了帝位后,他常对鲜卑人说:“汉民是汝奴,夫为汝耕,妇为汝织,输汝粟帛,令汝温饱,汝何为陵之?”又对汉人说:“鲜卑是汝过客,得汝一斛粟、一匹绢,为汝击贼,令汝安宁,汝何为疾之?” 此外,《北齐书》中有“汉辈”、“狗汉”、“汉老妪”等称;《北史》中有“汉家”、“汉地”、“痴汉”、“汉小儿”、“汉妇人”、“贼汉头”、“空头汉”等称;《宋书》中有“汉女”、“山东杂汉”等称;《南齐书》中有“不专汉人”、“母是汉人”、“通胡汉语”、“胡木汉草”、等语.
上述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,“汉人”一词在南北朝时期已完全脱离了“汉朝之人”的本义,用以指称同鲜卑等游牧民族相区别的民族共同体,并已完成了由他称向自称的转变.诚然,上述史料也反映出当时民族之间不平等的事实,集中体现在鲜卑人对汉人的歧视上.个中缘由,本文认为主要有二:其一,鲜卑人入主中原,与汉人争夺中国正统,故而有意贬汉;其二,鲜卑人生性剽悍,觉得汉人柔弱怯懦,故而轻视汉人。
值得注意的是,南北朝时期“中国人”的内涵发生了变化,不再像先秦秦汉时期那样仅仅指称华夏族或汉人,而是扩大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原地区的人们.这是因为石勒、苻坚、拓跋氏等曾统一北部中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以“中国皇帝”自居,要求共享“中国”称号,所以必须扩大“中国人”的内涵,将其与“汉人”区分开来,从而把本民族纳入到“中国人”的行列中去.这些异族好奸诈。
进入隋唐时期,继续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.与其说隋唐是汉人王朝,不如说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的联合王朝.隋唐时期,除了沿用“华夏”等称谓,以及使用“隋人”、“唐人”等称呼外,更多的还是用“汉”作为族称.《隋书·梁睿传》:南宁州“其地沃壤,多是汉人.”《旧唐书·温彦博传》:朝臣多主张将突厥降人“分其种落,俘之河南,散属州县,各使耕田,变其风俗,百万胡虏,可得化而为奴.”《旧唐书·元王寿传》载鸿胪卿元王寿谓突厥颉利可汗言:“汉与突厥,风俗各异,汉得突厥,既不得臣,突厥得汉,复何所用?”《旧唐书·李绩传》:“蕃将号徐舍人者,环集汉俘于呼延州,谓僧延素曰:‘师勿甚惧,予本汉人,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.’”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载高昌童谣云:“高昌兵马如霜雪,汉家兵马如日月.日月照霜雪,回手自消灭.”《旧唐书·穆宗本纪》中有个颇为有趣的记载:“陇山有异兽如猴,腰尾皆长,色赤青而猛鸷,见蕃人则跃而食之,遇汉人则否.”蕃汉之别兽类竟也察觉得到.
在《旧唐书》里,“汉”、“汉人”、“汉官”、“汉使”、“汉将”、“汉兵”、“汉军”、“汉骑”、“汉俘”、“汉家”、“汉辈”、“汉疆”、“汉界”、“汉城”、“汉关”、“汉仪”、“汉法”、“汉天子”、“蕃汉”等名词不胜枚举,唐诗中此类词语也屡见不鲜,如边塞诗人岑参诗云:“花门将军善胡歌,叶河蕃王能汉语.”这些既反映出唐代民族交往之频繁,民族关系之密切,反映出“汉”这一族称应用之广泛.
五代继唐,大量使用“汉人”、“蕃汉”等称谓.后晋天福中,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上表指斥石敬塘“称臣奉表,罄中国珍异,贡献契丹,凌虐汉人,竟无厌足.”契丹右仆射、平章事张砺“始陷契丹时,曾背契丹南归,为追骑所获,契丹主怒曰:‘尔何舍我而去?’砺曰:‘砺,汉人也,衣服饮食与此不同,生不如死,请速就刃.’”足见是时汉与契丹之间文化风俗差异之大,人们民族意识之强.民族观念完全确立。
辽宋夏金元是中国民族重组的又一重要时期,汉人含义发生些变化。除“汉人”继续作为族称外,还曾以“燕人”、“南人”、“契丹”代称汉人.经过长期整合,最后重新统一到“汉人”上来.
明清时期,汉族族称不似辽金元三代那样纷繁复杂.明代主要称“汉人”,间或使用“华人”、“明人”、“中国人”等称谓.清代汉族称谓进一步单一化.“汉人”与“满人”相对而称,如顺治谕曰:“满汉人民,皆朕赤子”,而“华人”、“中国人”则包括满人在内,并逐渐成为与外国人相互区别的称谓.
综上所述,从魏晋南北朝至辽宋夏金元明清,在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时间里,中国就像座大熔炉一样不断地陶冶、铸造着中华民族.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民族不断发展壮大,其族称经历了由纷繁复杂到趋向统一的整合过程.到清末以前,随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,汉族族称的整合过程基本结束,但“汉”与“族”尚未组合成一个复合词,“汉族”一词尚未出现.到清末才出现汉族这个词。